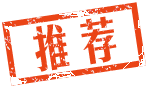|
文革中, 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70年代中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我国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上面提到的从日本引进1.7米轧钢机设备是其中之一。此外,还从国外引进了13套大化肥设备。其中的一套放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市。为安装这些设备,湖南省省委组织部从湖南各地借调了一些能胜任英文口译的干部到筹建中的岳阳化肥厂当翻译。所谓借调,就是组织关系还在原单位,临时被借用给另一个单位工作。我也被选中了。
这样,我于1976年初来到了岳阳化肥厂。岳化筹建办的一个干部到火车站来接我,然后带我到了洞庭湖边上的工地。只见在一片已经平整了的土地上,已盖好了一排排简易的工棚。大部分都已住上了工人。化肥厂的地基已打好,筹建办办公室和外国专家招待所等也已经建成。我首先被带到了工棚那里。借调来的翻译多数已经到达。使我喜出望外的是,他们大多是外交部留在湖南各地的干部,其中有我的同学任丙磊。还有几位是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高校的英语老师。我的学生肖云南也在其中。原来是外交部的人特别的高兴。外交部有人三年前曾对湖南省委组织部打过招呼,说我们这批人政治上不可靠,不能做外事工作,不能接触外宾。现在这个规矩看来是被打破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办公室。这是一个单独的小院,是专门为外国专家盖的。岳化筹建办下设立了一个外事联络办公室,简称外联办。外联办的主任姓黄,副主任有两个,一个姓廖,另一个是我们外交部干校的战友程法及。老程原来是外交部西欧司处长,解放前是地下党员,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文革中被怀疑有历史问题,长期隔离审查。湖南干校解散时已经查清,不存在什么问题,但仍被认为是不可靠,被分配在湖南医学院当英文教师。
岳化安装的有两套设备,一套是从美国Kellogg公司进口的合成氨设备,还有一套是从荷兰某公司进口的尿素设备。我们到达不久,两个公司派来的专家也先后抵达。我先后担任过材料、焊接和锅炉等方面专家的翻译。中国冶金工程公司第九分公司负责设备的安装,总工程师是一个上海人,十分精明能干。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都很高。他们能根据图纸进行设备的安装,只有少数地方需要外国专家的指导。
在工地上做翻译是很辛苦的。要跟着专家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有时要攀到很高的作业点上,如合成炉的顶部。每次爬行在脚手架上,特别是走到高处时,看着四周空空荡荡,往往一阵头晕,感到十分恐惧,害怕脚一滑,摔得粉身碎骨,永远也见不到自己亲爱的妻子和儿子了。但我还是硬着头皮,一次一次地挺过来了。工人们告诉我,每一个这种大型工程施工过程中没有不死人的。我听到这话后不久,就有一个工人在经过一个大型吊车时被掉下的大铁钩砸死了。为了赶进度,工人们经常加班加点,我们也要跟着加班。1977年年底,开始安装几个大型反应炉。那时天气十分寒冷。我们在萧瑟寒风中与外国专家以及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挑灯夜战,经常要干到12点以后。
照片NO.7: 作者(右一)和两位外国专家和翻译肖老师在工地上
我们几个学英语出身的人做专家翻译都没有什么困难。外国专家有时要给我们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讲课,做这种翻译难度大些,只有少数几人能做,我是其中之一。当我做这种翻译的时候,我的学生肖云南总会坐在下面认真地听讲。后来,她对我说:“在毕业后的岳化外联办翻译训练中,我真担心会被淘汰,在众多领导面前口译,第一次我很紧张。您坐在藤椅上镇定自若,不紧不慢地翻译着,给了我很大鼓励。榜样哦!那时我也跟您学了不少。老师不仅在专业工作上,在为人处事上都是好榜样。”后来肖云南进步很快,建筑公司和厂筹建办领导会见外国专家时,常常请她当翻译,开始几次有些紧张,后来慢慢也老练了,和我一样镇定自若。当时外联办专家招待所有一位年轻干部叫刘克利,长得很英俊。肖云南和刘克利谈上了恋爱,后来结为夫妻。两人都被分配在湖南大学教书,都成了教授。刘克利曾任湖大校党委书记、副校长。
大多数外国专家对我们都十分友好,与我们的关系都不错。但我与一个焊接专家闹过一次别扭。这位专家是英国人,因为年纪轻,应他本人要求,以他的名字相称,翻译们都叫他David,不懂英文的人叫他大伟。此人常常摆出一付英国人常有的傲慢相。平时常爱说一些当时被我们认为不友好的话,譬如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穿得像你们中国人那样难看,那么破的!” “你们说你们这里安全,没有小偷,那你们为什么每人办公桌的抽屉上都挂着一把锁?”一天下午,大伟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晃了一下脑袋,意思是让我跟他去工地。我连忙站了起来,走到门口,他拿出一张外国报纸,对我说,“你看,大陆又有一个飞行员驾机逃到台湾去了。” 说着把报纸往我手里送,我没有接。这时他还继续说:“你们这里已经有好几个飞行员飞过去了。你们这里没有自由,所以……” 开始我没有什么反应,后来突然想起,刚才他在办公室门口说话时,有一位老翻译在办公室,他可能听到了大伟说的话。如果他报告上级,说大伟策反,而我不作任何反应,我的麻烦就大了。想到这里,就严肃地对他说:“请你不要胡说八道!”,并立即转身回到了办公室,以此表示对他的抗议。此事按道理是应当向领导汇报的。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做。但又担心那位听到他说话的翻译向领导反映,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第二天上午,大伟又出现在我们办公室门口。他板着脸,对我晃了一下脑袋,我走出办公室,与他一起走到了工地。他东溜溜西溜溜,既不与我说话,也不与工人或技术人员讲话。这样溜了一圈就回办公室了。下午又这样重复了一遍。但第二天,他的态度好了一些,因此我对他的态度也恢复到以前一样了。大概我对他的抗议起了作用,此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事件。我所担心的事也没有发生。
我在岳阳化肥厂一直干到了1978年10月。那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由于与外国的交流和合作迅速发展,北京需要大量外文干部。在这种形势下,我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岳化外联办主任在专家招待所专门设宴欢送我,所有翻译和外联办干部都参加了。主任讲话,赞扬我为岳化建设作出的贡献。翻译们脸上的表情很不一样。肖云南对我说,她从心底里为我感到高兴。原来是外交部的翻译,有的人,如外联办副主任老程已经调回北京,有的调动已经有了眉目,因此脸上阳光灿烂,也有的调动还没有什么消息,脸上是一片阴云。我当然感到非常高兴。
我又一次登上了洞庭湖畔的岳阳楼。我不知来过这里多少次了。这次,我的心情和和以前大不一样,面对着八百里洞庭,感慨万千,想起了北宋大思想家和大文学家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对洞庭湖的描写:“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那时中国历史已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我的人生也揭开了新的一页。我当时的心情,与900多年前范老先生的心情似乎一模一样:“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