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正和岛
推荐语:“拼爹”,你未必就能成功
推荐人: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资本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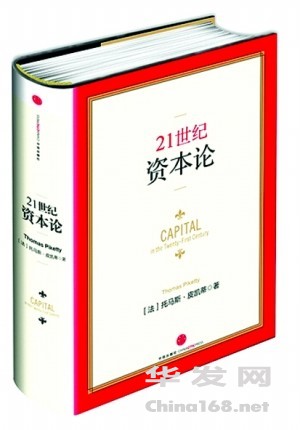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通过收集自18世纪以来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家庭与个人财富资料,对多国跨两个多世纪的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图景进行详实分析和解读。比如书中提出,当前在美国,10%最富的人掌握了全社会48%的财富,而1%最富的人掌握了20%的财富。在皮克迪教授看来,现有的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对于皮克迪所说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年代以及未来世界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时代”,这一结论值得商榷。比如,今天美国1%最富、10%最富的人群跟50年前、100年前的最富群体有多大的重叠?如果“最富1%”、“最富10%”群体总在不断变化、社会阶层流动程度足够高,那么,即使最富1%的收入占比很高甚至越来越高,“拼爹”就未必能保证成功。所以,收入集中度的提升跟“拼爹时代”不是一回事。
那现今贫富差距有多少是制度所致,多少是现代经济客观本质所致?从皮克迪、斯蒂格利茨到其他学者,都认为改变资本制度是纠正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而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财富分配上。
如果用实物作为财富的度量和成功的象征,只会把商业、把财富分配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零和博弈下的创业难有价值创造。因此,就有了基于信用货币的现代经济之前人类社会普遍鄙视商业、鄙视创业。
在价值的度量衡被信用货币化、财富被金融资本化之后,由于资本量不受实物量的制约,社会的金融财富总量是没有上限的(就像从中国金融财富总值在数量级上不断上升中所看到的那样),每个人可以追求的收入与财富也没有上限,尤其重要的是企业家、创业者所能得到的财富不一定是以挤掉别人的财富为前提,而是纯粹的新创造!
腾讯公司只有几栋办公楼,但它的总市值却超过1.1万亿港元;阿里巴巴集团上市后的市值也会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等等。是对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货币化结果,是对未来定价的结果,不是基于过去成本投入、土地投入、劳动时间投入的多少而定的。腾讯股权、阿里巴巴股权所代表的金融财富不是靠取代或挤压其他财富所得,是中国财富的纯增量。
到今天,皮克迪、斯蒂格利茨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土地分配,也不把注意力专注于机器设备、厂房等有形工业资本的分配结构上,而是到金融资本上找“掘墓人”。
于是,在今天的世界,谁掌握更多的金融资本,谁就更能在收入竞争中胜出。那么,金融资本在不同群体中的分配差距是否会最终把人类带向革命呢?是否真的是“这次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说金融化与现代技术带来的赚钱方式变革只是“肥了”金融资本家,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利益。但是,基于金融资本的PE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也使众多草根出身的创业者成为亿万富翁——李彦宏、马化腾、俞敏洪等这些新一代亿万富翁,如果我们还是处于没有货币化的土地财富和产业资本时代,他们即使再有能力,也不太可能实现自己的创业梦!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带来了更好的草根群体上升通道。
新兴行业也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共享、消费均等化,特别是在缩小不同收入人群间的知识与信息鸿沟方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看到本书,我们会本能地想到要通过制度调整,去强行“纠正”收入分配,而忘记在现代经济体里最为根本的是消费分配,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财富分配结构。
在这个层面,我们或许能清晰看到:19世纪以来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国家不是法国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而是在财富分配更不平等的美国。
这一状况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
第一,定位于人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第二,为不幸运者提供底线社会保障,确保每个人能够享有体面生活;第三,通过更加自由的货币化、金融化,给能者提供最大化发挥潜力的正面激励。只要能做到这些,成功者实现的合法收入再高,我们都应该为他们庆祝。
-----------------------------
正文:
作者: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
根据《福布斯》的报道,1987年全球只有140名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但如今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超过了1400人(2013年数据)。1987年这些亿万富豪的资产占全球私人财富总额的0.4%,但2013年该比例达到了1.3%,这超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夜的历史最高水平。
财富形成规模即可高速增长
《福布斯》排行榜中最令人惊奇的现象之一就是,无论财富来源于继承还是创业,一旦财富超过了某个规模门槛,那么就会以极高的速度增长。当然,我们并不能高估这些排行榜推断出来的结论的精确性,但事实本身还是非常有趣的。
首先来具体分析全球财富分布顶端的情况。在1990〜2010年间,全球操作系统巨头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的财富从40亿美元增长到500亿美元。盖茨的财富属于典型的创业所得,盖茨在《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当“首富”超过10年。与此同时,全球化妆品巨头欧莱雅集团的继承人利利亚娜·贝当古的财富从20亿美元增长到了250亿美元。盖茨和贝当古两人的财富都在1990〜2010年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增速约为每年10%〜11%。
换言之,这辈子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天的利利亚娜·贝当古的财富增速与高科技巨擘盖茨的财富增速相同,当然盖茨在退休之后其财富也在保持同样的高速增长。一旦财富形成,那么资本就会按自身规律增长,而且只要规模足够大,那么财富可能会连续高速增长长达数十年。
请特别注意,一旦当财富达到了一定的规模门槛后,资产组合管理和风险调整机会就可形成规模效应而产生优势,同时资本所产生的全部回报几乎都能用于再投资。拥有这样数量财富的个人每年只要拿出总财富中几乎可忽略不计的部分,他也足以过上极为奢华的生活,因此他的全部收入几乎都可用来再投资。这是最为基本但至关重要的经济机制,对财富的长期积累和分布有着重大的影响。
例如史蒂夫·乔布斯,这位伟大的创业者所获得的崇拜和追捧与比尔·盖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财富全部来源于其天才式的创造。在2011年,乔布斯达到了职业生涯顶峰,但在当年苹果公司股价高点时,他所拥有的财富大约是80亿美元,只有盖茨财富的1/6左右以及利利亚娜·贝当古的1/3左右。在《福布斯》排行榜上,还有数十人所继承的财富都在乔布斯之上。
遗憾的是,《福布斯》和其他报刊推出的财富排行榜大大低估了继承财富的规模。对于那些最大规模的继承财富,即数百亿美元或欧元级别的财富,那么或许可以假定,大部分资金依然存在于家族企业(例如持股法国欧莱雅的贝当古家族以及美国沃尔玛集团的沃尔顿家族)。如果情况如此,那么这些财富会和比尔·盖茨或史蒂夫·乔布斯的财富一样易于计算。但并非所有级别的继承财富都是如此:在10亿〜100亿美元的财富级别(按《福布斯》的报道,全球每年都会有数百新贵跻身这一级别)或在1000万〜1亿美元的级别,那么更多的继承财富是分散在投资组合中,那么报刊记者就很难去掌握这些财富(尤其是继承财富者往往不如创业者那样高调)。
征收财富税是唯一控制途径
无论如何,有关富人财富是否应得的讨论是没有最终答案的,因此当前迫切需要超越这种无效讨论。没有人会否认,社会发展需要创业、发明和创新。但问题在于,创业本身并不能让所有的贫富差距都合理化,无论差距是多么极端。以“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代表的不公平以及由于初始财富造成的资本回报差距将会导致资本的过度和持续集中:无论初始的财富差距是否合理,财富会自我生长并自我膨胀,会超越一切合理界限以及社会效用角度上的任何合理解释。
因此创业者会变成食利者,不仅是在代际交接过程中,在同一代人中也会出现,尤其是当人均寿命不断延长的今天:一个在40岁时充满了创意的企业家到了90岁就会变得极其保守,而他的子孙也不一定会像他那样具有创业才能。但财富却留了下来,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在20年里翻几番的情况。
这就是为何要在全球范围对大额财富每年征收累进财富税。这样的财富税是通过民主手段控制这种财富爆炸性自我膨胀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又可继续保持社会上的创业活力和国际经济开放程度。实施这种财税措施也是超越“财富道德关系”无效讨论的良方。赤裸裸的财富窃取是罕见的,当然也很少有财富是完全合理的。累进财富税的好处在于可以用灵活、统一和透明的方法来应对不同财富状况,同时让巨额财富置于民主控制之下,现在其实许多财富都已经得到民主控制。
不给富豪编一个道德排名
常见的情况是,有关全球巨额财富的讨论往往容易导向对具体某个人能力或品行的判断,这些判断往往带有脸谱化的专断特征。例如对现在的全球首富、黎巴嫩裔的墨西哥地产和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他就经常被西方媒体形容为靠政府庇佑下(暗指腐败)的垄断租金才积累了巨额财富,而比尔·盖茨则被塑造成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榜样。有时人们甚至会有这样的错误印象,好像是盖茨本人发明了全部的计算机和微处理器,如果他对生产力发展以及对全球福利的贡献能获得相应的酬劳,那么他的财富应该是现在的10倍(幸运的是,自从他退休之后,实际上地球上的好人才成为了他“积极外部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这种对盖茨的顶礼膜拜反映了现代民主社会要将贫富差距合理化的不可遏制的需求,对盖茨的膜拜仅仅是这种需求的副产品。然而在我看来,盖茨实际上也在通过对操作系统的实质垄断获利。此外我还认为,盖茨的贡献也要依靠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在电子和计算机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如果没有这些人所做的铺垫,盖茨的创新也就无从而生。但可惜这些默默无闻的研究人员并未将其每项工作都申请专利。总之,在没有对事实进行基本审查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将卡洛斯和盖茨置于正邪两端,是极为不合理的做法。
因此最有益的做法不是去给富豪编一个道德排名,这种做法常常最终沦为给西方唱赞歌的举动,最好还是要去理解财富动态变化背后的普遍规律,即只讲财富而不讲个人,并由此思考相应可以普遍适用而不用考虑其具体国籍的监管,尤其是财税监管。
中国资本管制的优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富裕国家提倡完全和绝对的资本流动自由化,没有控制,也没有各国间关于资产所有情况的信息分享。诸如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国际机构,以经济科学最新发展的名义来推销同一套措施。但是,这一运动本质上是由民主选举政府推动的、反映了特殊历史时刻的主导思想,苏联解体和对资本主义自动调节市场的无限信心是这一时期的标志。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方式是否明智遭遇严重质疑,富国很可能将增加资源在未来数十年进行资本控制。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发展中世界已经展示了其道路,那次危机让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巴西和俄罗斯相信,国际社会指示的政策和“休克疗法”并不总是明智的,是时候设定自己的道路了。那次危机也鼓励一些国家积累额外的外汇储备。这可能不是对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最佳反应,但是它有如下优势:单个国家在不丧失主权的情况下即可应付经济冲击。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一些国家经常实施资本管制,不为完全解除资本流动和经常账户管制的大潮所动。中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其货币从来都不可自由兑换。中国也严格控制进入的资本和流出的资本。资本流出问题目前在中国非常敏感,是中国资本管制模型的核心。这就引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中国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是不是他们财富的真正所有者?例如,如果愿意,他们能不能把钱转出中国?毫无疑问,中国的产权概念和欧美是不同的。它依赖于一套复杂且不断演变的权利和责任。举个例子,一个取得中国电信20%股份的中国巨富,想要带着家人移居瑞士,同时继续保留他的股份并收取数百万欧元的股息,相较于一个俄罗斯寡头,他这样做很可能非常困难。这一判断基于这样的事实,经常有大量资金离开俄罗斯去可疑的目的地。这在中国从未见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在中国这似乎控制得更严格。上述问题可能是众多原因之一。
我不是要为中国的资本管制制度辩护,不过,资本管制是管理和遏制财富不平等动态的一种方法。此外:中国有比俄罗斯更加累进的所得税,尽管它仍然不够累进。所得税带来的收入投入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其规模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愿意,尤其是如果其精英阶层同意,那么中国显然足以实施我此前讨论的累进所得税和资本税。在某些方面,中国比欧洲更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因为欧洲必须应付政治分裂和税收竞争的特殊紧张局面,这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到来。(本文摘编自《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