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章来源: 逆音
Carsick Cars主唱张守望:一直在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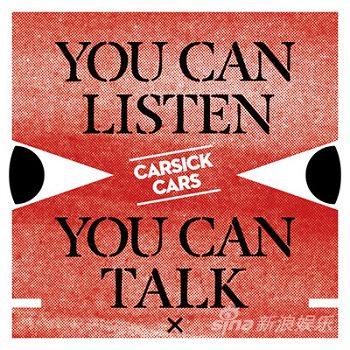
(逆音 记者/赵丛 摄影/赵大宝 汤庭)“北京地下音乐——‘非北京’的骄傲是22岁的摇滚神童张守望。”美国古典音乐评论家Alex Ross在他的一篇名为《中国古典音乐的大跃进运动》的评论文章里如是说道,“我第一次去北京D22酒吧的那晚,他表演了一首独奏曲,稳定的嗡鸣声之上是狡猾的极简主义的模式,有意识地从安静、简单的和声滑向阴暗的半音阶领域。张守望以历史悠久的齐柏林飞船乐队的手法,用(他之前小心涂过树脂的)小提琴弓演奏吉他。”
在过去的4年里,张守望已以出众的音乐才华及多元化的风格成为了北京新声力量最杰出的代表。随着今年1月他跟沈静的WHITE组合向美国先锋作曲家Glenn Branca致敬的第一张专辑的发行,我们知道了Maybe Noise这个由国内独立唱片公司兵马司成立不久的噪音子厂牌,而张守望自己作为厂牌负责人还在挖掘和发现更多的新声音;而随着他的摇滚乐队Carsick Cars与嘎调乐队一起历时39天跨越15个城市的公路巡演——“伟大航路”的结束,我们也曾迎来过那次巡演令人激动万分的谢幕演出以及Carsick Cars的第二张正式专辑《You Can Listen,You Can Talk》。
乐手档案:张守望(Carsick Cars)
Carsick Cars 演出、新专辑以及成长
逆音:在那次“伟大航路”的巡演过程中,有什么好玩或尴尬的事让你记忆深刻?
张守望:最刺激的一次是我们在香港演完出一堆人坐巴士回宾馆,我以为有人会拿我的效果器箱子,但是下车之后我问我的箱子呢然后没人答应我,才发现箱子落在巴士上了,当时我脑子一下子就蒙了,如果箱子丢了接下来的巡演就没法继续。然后当地的一个朋友带着我一起追那辆车,大概追了十分钟最后追上了,当时跑得特别快,有点像电影情节,旺角黑夜什么的。后来和当地人说起来,他们都觉得惊奇,因为那种巴士通常跑的很疯狂,能追上是个奇迹。
逆音:对其中哪一站的印象最深?
张守望:其实对每站印象都挺深的,可能最深的是武汉那站,因为当时最后一首歌是跟AV大久保还有嘎调一起演了一首《I Wanna Be Your Dog》,还平生第一次“跳水”了。
逆音:然后那站之后还有类似于after party的演出,是吗?
张守望:对,是在吴维开的Wuhan Prison(武汉监狱),特别好玩的一个小酒吧,在VOX底下。它旁边有一古着店,里面就是个小酒吧,你可以在上面随便弹琴唱歌什么的。我们在底下演了一点不插电的歌。嘎调詹盼演了好多原来哪吒的歌,小怪物去天国还有圈,我唱了自己写的《Dead Flower》。
逆音:看到05年8月底王悦(前挂在盒子上乐队主唱)对你们做的一个采访,问你们最成功和开心的演出是哪次,你当初说的最成功的是向Joy Division致敬的那场,最开心的是第一次在学校公开排练,现在已经过去4年了,纪录一定也被刷新了,现在在你看来最成功和开心的演出是哪次?
张守望:可能有点多,因为演出实在太多了。现在想成功可能就是刚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音乐节,因为对于我来说它是欧洲最好的音乐节,有特别多我们特别喜欢的乐队来演,比如Neil Young、Sonic Youth、My Bloody Valentine。要说最开心,现在回想起我们刚开始排练内会儿确实特别好玩。
逆音:在国外演出最深的感触是什么?你感到国内国外音乐场景甚至是文化场景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张守望:其实在国外演出本质上跟在国内没什么差别,观众的反映跟国内的区别不太大,如果是好的音乐的话他们都会喜欢的。区别可能就是不管是从设备还是音乐节的服务来说都更专业一点吧,尤其各种细小的方面。比如说我们在瑞士演出,那个音乐节特别温馨,所有音乐节的服务人员会自己做饭给我们吃,工作人员和乐队都没有距离。音乐场景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在国外各种音乐类型早就有人玩过,新的乐队如果没有创新,很难有机会被观众听到。而国内独立音乐才刚刚起步,观众的欣赏层次也是有限的,这是本质的区别。
逆音:最憧憬去哪儿演出?
张守望:可能还是纽约吧,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去过那儿演出。我去过纽约两次每次都是待了一个月,都是自己的演出,但还是希望Carsick Cars可以一起去。我们计划十一月初会去,有可能参加CMJ音乐节。
Carsick Cars - 《You Can Listen, You Can Talk》
逆音:说说第二张专辑所呈现的气质吧?
张守望:第一张专辑特年轻和热血,有点不管不顾的。写那些歌的时候是十九岁,可能有的歌都是上高中时候写的词,现在四五年过去了,几个人都在成长,环境也在变,肯定新专辑的东西会更沉淀一点也更成熟。说到歌词,我写歌词都是一瞬间的感受,可能每个人对歌的理解都有不同,比如说标题“You Can Listen, You Can Talk”可以去形容很多很多你身边的事情。
逆音:封面的意思?我们讨论了一下,说觉得封面是一张人脸,两个大大的眼睛在监视着你,如果说它就是一张人脸的话,我注意到在嘴的位置是一个小叉子,其实是说你根本就没法做到“You can listen,you can talk”的状态,是吗?
张守望:对,当时设计的时候有这个考虑,而且设计的时候考虑到有的人会看到有两张脸向不同的方向看,也有一些寓意在里面。那张专辑封面确实有一些偶然性,但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有很多种解释。
逆音:我注意到Carsick Cars绝大多数歌都用的是第三人称,目前我只能想到歌曲《Invisible Love》不是,这是在创作表达上的特别考虑吗?
张守望:其实我用很多第三人称写歌是受鲁迅的影响比较大,他很多散文或者短篇基本上都使用第三人称。可能第三人称对我来说更容易一点,去写一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比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更客观。
逆音:之前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制作人是乐队的另一个成员。来说说新专辑的制作人Warton Tiers吧!说说这次合作,你们交流顺利吗?
张守望:我认识Warton Tiers是因为他在美国先锋作曲家Glenn Branca的《十三号交响》里面打鼓,他之前也跟Glenn Branca同是Theoretical Girls乐队的成员,他是鼓手。Theoretical Girls是我最喜欢的乐队之一,对我影响也挺大的。我第一次见他给他听我们第一张专辑的Demo,当时有一些沟通。他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音乐人,也参加过特别多纽约特别牛逼的乐队的专辑制作,当时知道能跟他合作确实挺兴奋的。我们录音的时候他花了非常短的时间帮我们找到了我们想要的声音,因为毕竟他除了是个制作人外也是个特别牛逼的音乐人,他很注重什么是乐队想要的,而不会把想法强加给你,整个录音都特别顺利。
逆音:跟上一张专辑相比,新专辑有哪些突破或者说是新尝试?
张守望:有些歌里我们加入了黑管、小提琴还有笛子,还有新专辑最后一首歌完全没有吉他、贝司和鼓,就是风琴跟唱,对于我们来说都算是新的尝试。另外,Warton Tiers在《Invisble Love》里弹了钢琴,他混音的时候在一天的尽头里加了吉他,可能是混着混着混high了就自己加了好多吉他。
逆音:乐队成立4年了在心态上有无变化?
张守望: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像写第一张专辑时候的心态,不管不顾什么都不怕,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新的乐队。做第二张的时候肯定就会考虑我们能做出什么新的东西能有什么突破,毕竟去国外演出看了特别多好的乐队,有一种竞争感,觉得我们能做得比其他乐队更好,做出一些更新的东西,这是最主要的心态上的变化吧。
关于守望这个人
逆音:最早是怎么接触到摇滚乐的,听的第一张摇滚专辑是什么?
张守望:第一张我听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第一次买的磁带。之后老去CD店买朴树、张震岳、花儿什么的,前些日子在朋友车上听花儿觉得还能勾起些上初中时候的回忆。后来接触的第一张国外的是Smashing Pumpkins,之后开始听Nirvana、地下丝绒、Sonic Youth,第一次听地下丝绒之后就觉得必须要组一个特别牛逼的乐队。
逆音: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吉他的?
张守望:其实大概我十四五岁时我妈送了我把吉他,之后我去新街口跟一个玩金属的人学了两节课,他教我弹小草什么的,学了两节我就不去了,因为我觉得弹吉他特别没劲,我指的是以他那种方式,但当时他让我觉得所有的人可能都是那么弹的,然后我就把吉他放那儿了好几年没弹。再后来我听了地下丝绒,发现吉他原来是可以这么弹的,之后就自己琢磨也没跟别人学。
逆音:什么影响了你?文化、音乐、乐队或者人?
张守望:影响我的人太多了。其实美国文化对我挺大的,不管是地下文化还是当时的垮掉的一代,还有美国的流行文化,对我影响都特别大。
逆音:除了音乐,平时还喜欢干些什么?
张守望:我之前比较喜欢摄影,拍一些黑白的照片。但后来因为得自己冲胶卷自己放大,花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就不拍了。
逆音:一般拍些什么?
张守望:我特别喜欢拍建筑,特别有几何感的建筑。
逆音:生在一个物质跟资讯更丰富的时代,我们得到很多东西都更容易了,比如说绝大多数专辑在网上都能下载,你怎么看待网络下载?会不会很怀念人们平常所说的“打口碟的时代”?有时候我就会觉得,那种靠自己一点点发现的更珍贵。
张守望:可能很多人会有你这种感觉吧,但我觉得有网络还是能节省你很多时间,因为你想要的东西可以很快就能找到。有打口的时候虽然会有你说的那样每次发现一个新东西可能会比现在更兴奋一点,但是那样花的时间会很多。而且我觉得现在乐队靠卖CD也完全挣不了钱,网络是个特别好的平台去推广你的乐队。包括这次在巴塞罗那演出,台底有很多人会唱我们的歌,这完全就是myspace的功劳。有一个西班牙大哥,他跟台下一直唱我们的歌,演完之后他碰到我们说你们是日本最牛逼的乐队,然后我们说我们是中国的,他也特别惊讶地说不好意思什么的。
逆音:你在去年为北京新乐团作曲的《西直门车流灯》,这算是在新的音乐领域上的第一步,说说创作跟这首歌首演时的感受吧。
张守望:当时新乐团找我作这曲,我之所以愿意去做是因为对我来说是个新的尝试,因为以前从来没做过类似这种把音乐写在谱子上让专业乐手去演奏的音乐。当时我挺兴奋的,也花了特长时间买了很多书去学,了解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做,因为之前可能我有很多的想法但没法把它实现到谱子上,或者把它告诉给别的乐手怎么去演奏。首演的时候挺成功的,那些乐手特别棒,也特别理解我那首曲子,我觉得当时演出的观众也都挺喜欢那首曲子的。
逆音:你已经先后跟Glenn Blanca、Blixa Belgard、John Mayer、Manuel Gottsching、Elliott Sharp、Alvin Curran这些大师级的先锋音乐家或制作人有过合作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肯定有很多,有没有发现他们之间共通的地方?
张守望:当然每个音乐人肯定都有特别大的不同点,但我觉得他们共通的地儿是人都特别好。包括Sonic Youth、E.N.乐队的Blixa Bargeld和Elliott Sharp,我觉得人在某一个领域能做到一定地步,肯定人都特别好,他们明白怎么做人,才有人格魅力。
逆音:用一句话或一个词来分别形容一下Carsick Cars和WHITE吧。
张守望:Carsick Cars还是摇滚乐吧,毕竟那些根源的东西都是摇滚乐。WHITE,用一个词就是实验。
逆音:除了Carsick Cars跟WHITE两个乐队外,你也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吃声音”、“先锋音乐节”及“四把吉他”这样的噪音即兴演出,能在摇滚跟先锋音乐中找到平衡点吗?
张守望: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说是互相影响的。如果我只玩Carsick Cars,我可能会局限在摇滚的框架里了,玩WHITE的时候我会有好多其他的想法,我可能会觉得这个可以用在Carsick Cars上。我觉得对于WHITE来说,形式虽然不是摇滚乐,但是是有摇滚乐的能量在里面的。
关于Maybe Noise这个厂牌
逆音:Maybe Noise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最早知道是年初在WHITE的CD背面看到的。
张守望:是在今年1月成立的。当时因为Hot &Cold、Muscle Snog这些新的有些实验性的乐队出来,我觉得应该做一个这样的厂牌去推广这种音乐,因为毕竟北京现在的环境还是以摇滚乐为主,年轻的乐手可能没有一个平台去做一些新鲜的东西,有这么个平台应该会比较好玩。因为像在纽约,做乐队如果没有实验性的话会被别人看不起的。
逆音:Maybe Noise是兵马司的噪音分支厂牌,怎么给这个“噪音”定义?可以把它看作是选择乐队或音乐人风格的标准吗?
张守望:也不是标准吧,Maybe Noise的这个“噪音”是相对而言的,所有比较新鲜有实验性的音乐都比较符合我们的宗旨。
逆音:厂牌有多少人在运作,具体怎么分工,作为负责人的你主要负责什么?
张守望:我主要负责去发现一些好的乐队,比较适合Maybe Noise的,主要是联系这些乐队。之后的乐队录音或者发行这类事都是兵马司的Nevin在帮我,包括8 Eye Spy这张专辑,是音乐人杨海崧给他们制作的。
逆音:谈谈投资吧?
张守望:其实Maybe Noise是一个特别DIY的厂牌,投资非常少,毕竟这种音乐肯定不会像兵马司旗下的乐队有那么大的市场,所以还是比较DIY。比如说Muscle Snog的专辑,就是在自己家里录的,还有Hot &Cold、日韩的实验组合10也都是自己在家中录的音。
逆音:从乐手到厂牌负责人身份的转变,看问题的角度也会不一样?
张守望:肯定会不一样的,做一个厂牌你要考虑资金、市场这些方面的事,肯定还要帮乐队考虑宣传这方面的事情,以前做乐队肯定考虑的不会这么广。
逆音:6月20号,八眼儿(8 Eye Spy)跟冷热(Hot &Cold)在Maybe Noise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评价一下这两个乐队吧。
张守望:Hot &Cold是我一直都特别喜欢的乐队,他们的声音很奇特,他们听上去不像任何一个乐队。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如果在纽约的话肯定会已经特别有名了。我第一次看8 Eye Spy是Carsick Cars去南京演出时他们给我们做暖场,当时就觉得南京竟然也有这种No Wave的乐队,当时看得挺兴奋的。我觉得国内需要像这两个乐队这样的声音。
逆音:提到Hot &Cold就自然会想到Simon跟你还有王旭的Speak Chinese or Die乐队,什么时候会正式录几首歌?
张守望:我们之前在说这件事,因为Simon马上就要回加拿大上大学,我希望他走之前我们能录一些东西,希望有时间。其实挺可惜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越来越好了,但他一下就要去上学了。但他父母会留在北京,所以他夏天放假肯定会过来,而且大学之间肯定会有内种交换,他会试着过来待一年。
逆音:除了WHITE、Hot &Cold跟8 Eye Spy,还签了那些乐队?发行计划是?
张守望:还有Muscle Snog,他们在7月初的时候发行过专辑,但他们跟我说不会演以前的歌了,现在都是玩些即兴的。还有刚才说的10。之后可能会发行一张我跟杨海崧合作的专辑,是我录的吉他杨海崧念的一些他写的诗,这张的母带特别早就录了,但一直没有时间去弄,想先把第一批乐队的唱片给发了。
逆音:8 Eye Spy、Hot &Cold跟Muscle Snog都是弥勒厂牌旗下的乐队,说说这次跟弥勒的合作吧。
张守望:弥勒厂牌有好多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乐队,我觉得他们的运作方式也挺有意思的,但可能毕竟他们的资金跟人手很有限,我还是想借助兵马司的力量,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些乐队。
逆音:有没有很喜欢的国外音乐厂牌?
张守望:Matador,还有Mute,挺不错的。
逆音:说到Maybe Noise,好像兵马司唱片还成立过一个民谣子厂牌,是吗?
张守望:嗯,对,叫Maybe Horse(马儿曲)。
WHITE:无规则的大WHITE
逆音:三月份大WHITE组合以五人阵容出现在了先锋音乐节,演出反响好像还挺不错的,有没有想过把之前不固定人数的多把吉他合奏给坚持下去?
张守望:其实当时演完出我就想把之前几次大WHITE的那些东西录一下,可能没有时间,毕竟人特别多不太好组织,包括排练时间和录音。可能之后会有录音吧,但会以不固定人数的形式。
逆音:有没有考虑过加一些新的乐器?
张守望:其实这次先锋音乐节之前想过加一个萨克斯风还有些大提琴,但因为我之前要去台湾,时间太紧了。之后还是希望能把曲子写得更完美些,有更多乐器。
WHITE:与沈静的二人组合
逆音:WHITE组合的另一个固定成员沈静在伦敦,而你在北京,怎么完成创作的?
张守望:基本上都是每次演出之前,我们用特别短的时间排练。其实我们俩的合作挺奇怪的,几乎不用交流,我们只要一弹乐器就能配合得特别完美,而且每次排练我们俩都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创作出来。
逆音:说说今年4月底在英国几个城市举行的演出吧,是专场演出吗?演出是沈静联系的吗?
张守望:基本上都是WHITE,有一些暖场乐队。是在英国的一个叫Lin的中国人联系的,他在那边也玩一个噪音乐队。在伦敦那场是在Barbican艺术中心,当时有小河、FM3、颜峻还有巫娜,其他演出都是在小的俱乐部里。
逆音:去年底WHITE在北京演了三场,随着今年在Maybe Noise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且喜欢你们了,有没有对未来在国内其它城市进行的演出做个规划?
张守望:肯定会巡演的,但对于沈静来说,回来一趟不太容易。但8月份WHITE和Carsick Cars去台北参加一个大的音乐节。我们会提前大概一个星期去排练一下,然后准备第二张专辑,因为我刚给Lee Ranaldo发过邮件,他说他特别感兴趣给我们制作第二张专辑,具体的还没定,他说制作或者合作的形式都可以。
逆音:最后请推荐一些你最近在听的音乐,给看到这篇采访的朋友分享一下吧。
张守望:有个布鲁克林的乐队叫These Are Powers,主脑是Liars乐队以前的贝斯手。还有个也是来自布鲁克林的乐队叫Oneida,上次在西班牙我放弃了一半的Neil Young演出去看他们,因为他们真的特别棒,他们有两个成员是Ex-Models组合的。其实如果大家想去找些新的特别好的乐队,不妨可以上Pitchfork转转,它是个不错的音乐资讯网站,美国那些最新的特别好的乐队,在上面都有介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