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21世纪网
美国作家何伟

实习记者 司马原
“不做中国问题专家,只做一名想要理解中国的外国人。”
这是美国作家何伟对自己的定位。何伟在中国生活了近十年的时间,观察并记录这个国家,写成了他的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之后奔赴埃及,此次他重返中国是为了推广他的新书《奇石》。借这个机会,本报专访了何伟,请他谈谈他是如何理解中国的。
寻路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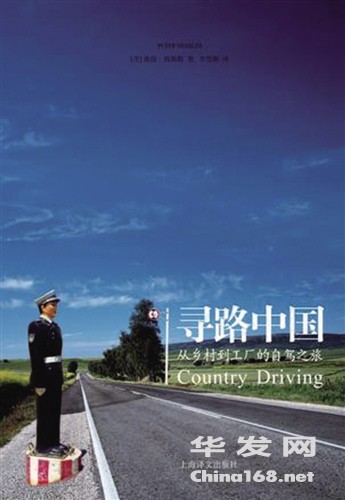
我对中国的认识没有根本性变化
《21世纪》:从1996到2007年,这段时间你几乎都在中国生活,这也是中国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你认为,在这十年中国发生了哪些主要的变化?同时,你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哪些变化?
何伟: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口流动,比如说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比较多;二是有不少人变成了中产阶级。像我的很多学生就是这样,他们大多是从农村来的,小时候家里面没有什么钱,但是接受了比较多的教育,大学毕业后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自身也变成了中产阶级。
现在我觉得中国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壮大。我认识好多中国人都曾出过国,一部分是读书,还有很多是出国旅游的,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很少见的情况。现在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北京和上海。
不过,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群体还没有形成。但是我觉得跟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当然是要更好。中产阶级的数量要大得多,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也高得多,生活条件也比以前稳定多了。
另外,我发现,最近几年内陆城市的变化可能要比北京上海更大。特别是内陆的省会城市,变得特别快。这些城市在以前都属于很偏僻的地区,但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交通变得很便利。我以前每次去重庆都坐船,现在那边有3条高速公路和2条铁路。
具体到我对中国的认识,发生最大变化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在涪陵的时候。因为当时刚到中国,发现很多,自己的变化也很大。但是离开涪陵之后,自己就没有那么多变化了,也比较稳定了。当然我也发现很多新的东西,但是根本的看法、角度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开始写作时往往没有确定的主题
《21世纪》:我们知道,你曾经是《纽约客》驻北京站的记者,当时,是怎样一种工作机制?你又是怎么确定选题的?
何伟:一般来说,如果是《纽约客》的记者,你自己要选写什么题目。我的文章都是我自己决定要写的,编辑没有直接告诉我什么。他们了解我是一个比较有思想的人,我也很喜欢中国,所以我文章的题目都是我自己决定的,这一点我也很清楚的告诉了他们。
有时候我开始研究一个题目,具体的题目我还不知道。我写过一篇关于药剂师的文章,我碰到这个药剂师的时候就感觉他身上有有趣的故事,但实际上我不知道这个有趣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我在中国也经常有这种感觉,慢慢采访、慢慢研究,发现我的主题,在开始的时候反而没什么确定的主题。我觉得这是最理想的、比较自然的一种方式。
我在《纽约客》没有基本工资,按出版文章的字数计算薪酬。一方面可以说没有稳定的收入,但另一方面讲也比较自由。如果我签了固定的雇佣合同,必须写多少多少书文章,那我写不了中国三部曲。2000-2007年我文章写得并不多,每年为《纽约客》写2-3篇文章,就是因为我比较重视书。写书是我的重点,特别是关于中国和埃及的书,这些地方比较复杂,可以用很长的篇幅来描绘这里的人物、特色。
《21世纪》: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比如说你写了一个题目,你报给了编辑,编辑说他不喜欢这个题材?
何伟:以前有,我曾经写过关于姜文的文章,他跟我谈了很多直率的想法,他也是个有趣的人。我把关于他的文章写好了,但是编辑决定不出版这篇文章,我也没有办法。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而且这是早些时候的情况。那时候我刚入行,还有很多东西不习惯。后来这样的情况就没有再发生了,现在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我和编辑都互相了解,配合比较顺利。这是非常独特的一本杂志,和一般的新闻媒体不一样,他们的作者都是比较独立的。
非虚构写作最重要的是真实
《21世纪》:你的著作多为非虚构作品,你如何理解非虚构写作?在有些时候,非虚构写作和虚构写作的界限是不是比较模糊?
何伟:非虚构就是所有内容都是真的,你不能创作。非虚构写作的创造性在于我怎么写、以什么样的风格。你必须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同时也可以借鉴虚构写作中的一些方法,这体现在写作手法、风格上面。
非虚构写作也和新闻报道不同。新闻报道要求时效性,非虚构写作不要求时效性。非虚构写作可以写得很长,新闻报道不能这样。此外,非虚构写作可以使用第一人称,但是新闻报道中一般不会这样。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区别,但是我觉得这三个是新闻报道和非虚构写作之间最大的区别。
《21世纪》:国内很多新闻媒体也很强调非虚构写作,但同时又想追求故事好看、有冲突,但是追求真实性看起来过于逼真,反而也有点不真实。我看美国普利策获奖作品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和小说这种虚构作品也没有太大区别。
何伟:20世纪60年代有一本书叫做《冷血》,杜鲁门·卡波的这部作品也是非虚构作品,非常好看。但这部作品引起了争议。此后,非虚构写作非常强调内容要保证真实性,不能有任何创造,但是风格可以与虚构作品相似,这个是没问题的。最重要的是真实。有时候非虚构作品出现虚构的问题,就在于作者的采访不扎实。
《21世纪》:无论是在涪陵地区还是在三岔村,你都成功地融入了当地。我很好奇的是,你是如何融入当地社区,建立自己朋友圈的?
何伟:在涪陵的时候,我不是记者,我是老师。身份的不同使得这本书也比较特殊。在三岔村的时候,我的目标不是写东西,而是要找房子、要去农村熟悉一下,没有想要写书,但后来观点慢慢改变了,想写成文章发在《纽约客》上面,才开始对他们的正式采访。发表文章以后就翻译过去给他们看,说要写书,征得他们的同意。
在写《寻路中国》的时候,我是一名记者,我选择的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地方,采访的地点也都比较小,可以单独聊天。有时也会遇到障碍,比如在丽水的工厂老板,但是不多。像我在丽水的时候,那里大多数人口都是外来的,外来人的思想比较开放,跟他们的语言也有关系,他们互相之间都说普通话,我听得懂,这也是我选择丽水的一个原因。
《21世纪》:你的写作一直侧重细节和样本调查,你对有关中国宏大叙事的写作题材有没有兴趣?关于中国何去何从的思考是不是会更引人关注?
何伟:我在江城的那段时间,我的重点就是我现在是一个观察者。如果要写这个地方的什么细节,人物是什么样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涪陵是什么样的城市,我希望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可以通过我的书了解到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如果我写的时候就说,15年后的中国是怎么样的,可能现在都是错的。
我觉得我喜欢的不是中国的未来,而是我看到的现在的中国,地方上的普通人的生活。我对政府这块领域不是很感兴趣。我也会写当地的一些干部是怎样的,比如涪陵的一些领导,但是不涉及高层的领导。
焦虑也是一种时代进步
《21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是从对中国人的评价开始的,比如中国人的气质和性格等等,你对中国人的总体评价是什么?比如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焦虑感,这是一种中国病还是全球病?
何伟:中国人的性格不是太外向,从采访中就可以发现,他们不会一下子告诉你很多私人的东西。美国人爱说话,特别外向,埃及人也这样,但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以前可能担心外国人不懂他们,但这种情况也在慢慢改变。以前中国人不是很自信,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很多人成功了,然后他们开始出国旅游,有更多和外国人交流的机会,和外国人交流就变得不会那么不舒服了。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中国人以前是很封闭的,尤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九十年代开始已经好多了。
我觉得,美国社会已经发展得相对比较成熟、稳定,所以相对就不那么焦虑。中国仍然处在改变的阶段,焦虑是很自然的,今后可能会不一样。特别是文化水平比较高,对未来想得比较多的群体。但这些年,美国卷入很多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而中国的重点是在发展自己国家上面,而且也很有效率。
过去的时代,中国人好像更传统一些,焦虑感也比较少。现在大家要想得就更多了,比以前更忙、压力更大,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是进步的一种表现。
作者:王尔德 司马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