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 北京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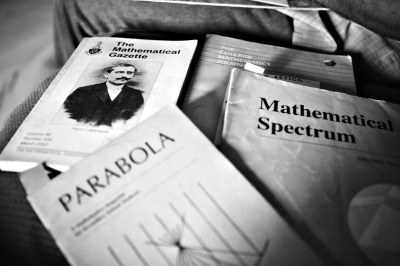
访华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威斯康星大学阿士凯教授和我都是从事纯数学研究的,也都从事过现代数学史研究,晚年又都专注于数学教育,经历颇为相似。
阿士凯教授拿出一张纸,写下国际数学与科学测试中,针对8年级学生的一道分数相减的计算题:问1/3-1/4=?这是道选择题,有四个选择答案。答案之一是分子分母分别相减,即(1-1)/(4-3)。这一答案当然是错的,但是选择的学生还是很多,国际平均占参赛学生的25%,日本学生中选此答案的占到10%,韩国小于3%,而美国则为32%。
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学生“喜欢”这一答案,为什么?令人不解。大家知道,分数相减的正确答案要用通分方法求得。获得正确答案的学生,国际平均只占总数的37%,日本有65%,韩国高达87%,美国只有29%。这就是说,经过基础教育的多数美国人,未来将不会做分数的加减法。阿士凯教授问,如果中国也参加国际数学与科学测试,成绩会怎样?我觉得大概会和韩国差不多。阿士凯教授于是说,中国不要向美国学习数学教育。日本就是因仿效美国的数学教育,学生成绩不断下降。事实上,1980年代日本学生在国际测试中的数学成绩曾经位居世界第一,以后渐渐落后,现在已经比韩国差一大截了。
我的看法是,中国数学教育得益于基础扎实。在中国,要求学生使用通分方法做分数加减,属于基本技能的训练。基本训练,往往很枯燥,学起来不怎么愉快,也没有太多的道理可讲。教学上只要按部就班,一丝不苟,熟练准确,养成习惯就好了。这种教育理念,初看好像不大符合近来时髦的“创新”、“发现”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可是我国的一线数学教师依照传统而行,严格训练,绝不走样。在阿士凯教授看来,美国缺的就是这种朴素的有关基本技能训练的教育理念。
我向阿士凯教授请教的是对一篇文章的看法。2012年7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位政治学教授的文章,题目是:“学习代数是必要的吗?”文章认为,学生学那么多的代数没有用,浪费青春。我请他发表评论,阿士凯教授自然是极力反对。
美国数学教育“忽视数学内容”的现象,有很深的历史根源。美国D.克莱因有一篇文章,梳理了美国百年基础教育的历史。其中提到,20世纪初,美国的数学教育曾被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所左右。杜威教育学说的传承人W.H.克伯屈曾是一位数学教师,后来投入杜威门下。他在1920年代曾有两段十分雷人的话:“就日常生活中的思维类型而言,数学害大于利。现有中学的代数学和几何学的学习不应继续下去”;“我们过去教的代数和几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我读到这一段,也是惊诧莫名。因为克伯屈在数学教育里推行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美国中学生选修代数的人数比例,由1910年的56.9%下降到1954年的24.8%。阿士凯教授说,1960年代的新数学运动,目的是要加强现代数学内容。那时,一批真懂数学的数学家,已经用通俗的笔法写了教科书,可是大部分数学教师还是根本看不懂。后来新数学运动自然是失败了。归根结底,仍旧是美国数学教师的数学水平跟不上。
这次会面之后,我一直在想,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愉快教育,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说得十分动听。但是忽视对“数学内容”的研究,缺乏数学知识的系统性,具有致命的缺陷。我们如果紧随其后,亦步亦趋,将来会不会像美国数学教育那样,弄得学生做分数加减法也大量出错?如果不认真对待,任凭“去数学化”思潮泛滥,后果真的很难说。
阿士凯教授说,现在美国大学里的数学教授,80%都具有在国外接受基础教育的背景。美国的大学研究生水平虽好,但是基础教育不行。在我看来,阿士凯教授表达的是美国式的忧患意识。我们也有自己的忧患:数学英才教育的缺失。美国的一些优秀中学生,已经在学习多变量微积分和群论,接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走上DNA、RNA的分子生物学前沿,可是我们的一些优秀生却在为争做“高考状元”而深陷题海。
来源: 北京日报 |
|